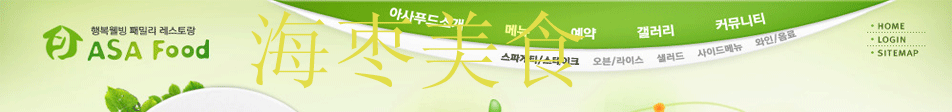|
在中国历史上,有很多民族曾经叱咤风云,对历史的进程起了重要的作用,如匈奴、鲜卑、突厥等。但辉煌一过,它们就逐渐湮没在历史长河中,甚至踪影皆无。契丹族就是这样一个民族。 自契丹族领袖耶律阿保机于年建立辽朝至年辽亡,多年间,契丹的铁骑纵横于北中国,建立了一个与北宋相抗衡的庞大帝国。年辽被金灭亡后,其残余力量仍在耶律大石的统率下,远征中亚,建立了史称为西辽(穆斯林和西方史书称之为“哈喇契丹”)的王朝,统治中亚地区达90余年,直至年被蒙古所灭。西迁的契丹人只是很少一部,并在西辽灭亡之后逐渐融合于当地的民族。金朝统治下的契丹人中的一部分被迫南迁,后逐渐汉化,到元代成为汉人中的一员。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长城以北,这些契丹人后来大都与女真、高丽、蒙古族融合,相当一部分随着蒙古大军的四处征讨而分散到全国各地。这样,契丹作为一个民族,到元代中后期就已经不存在了。 那么,今天是否还存在着契丹族的后裔呢?这个问题很早就引起了人们的 达斡尔人传说其祖先几百年前在首领萨吉尔迪汗的率领下,从原来“散居西拉木伦,哈拉木伦地方”也就是今内蒙古巴林左旗一带迁居到今内蒙古莫力达瓦达斡尔自治旗一带修边堡,从此便在这里定居下来。这一传说有其历史背景。金朝为了防备北方诸多蒙古部族的侵扰,曾大规模地修筑界壕,界壕是包括城墙、壕沟以及边堡在内的立体防御体系,也就是金代的长城。由于界壕的修筑需要大量劳动力,而萨吉尔迪汗率领的契丹人可能就是被金朝强迫征发而来的。另有文献记载,辽亡后,曾有一部分契丹遗民在库烈儿的率领下向北迁徙,今黑龙江根河以北仍有库烈儿山,直到明末清初,根河一带的达斡尔族酋长根铁木儿还被通古斯人称为契丹酋长,而达斡尔族一直供奉的本族菩萨也名为库烈佛。 刘凤翥先生《从契丹小字解读达斡尔为东胡之裔》(《黑龙江文物丛刊》年第1期)一文认为,达斡尔语中“长”(“首长”的“长”)一词是因袭契丹语,“兔”、“乌鸦”与契丹语相同,“马”、“山羊”、“蛇”、“狗”等词源于契丹语,“仲”、“冬”、“族”等词的发音达斡尔语与契丹语相同或相近。他据此得出结论:“像‘马’、‘山羊’、‘狗’、‘兔’等狩猎民族和游牧民族最常用的语词,很难用借词来解释,它必然是自古流传下来的。语言的因袭必包含着民族成分的继承。由此,我们可以推测,达斡尔族是元灭金之后,由留居当地的契丹人逐步发展起来的。” 达斡尔族的狩猎、捕鱼方式与契丹人大致相同,达斡尔族至今保持同姓不通婚的习俗与契丹族也相同,达斡尔族的祭天仪式与契丹族的祭天有相通之处,达斡尔族与契丹族都信奉萨满教,而最具达斡尔族特色的传统体育项目曲棍球很可能源自辽代契丹族的马。 尽管近年来云南契丹后裔成为新闻热点,但这并不是什么新发现,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有人向云南民委反映契丹后裔的情况,但未引起重视。而到20世纪90年代,内蒙古社科院的达斡尔族学者孟志东、云南学者杨毓骧以及内蒙古大学的陈乃雄教授、黑龙江省文物考古工作者干志耿、叶启晓等都先后对滇西保山地区的契丹后裔进行过调查、研究,他们都有文章与著作问世,尤其以孟志东的《云南契丹后裔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年版)一书为全面。 云南的契丹后裔分布在保山、临沧两市和德宏、大理、西双版纳等自治州,他们自称为“本人”,共约15万人,其中保山市的施甸县是契丹后裔的集中居住地,以阿、莽、蒋三姓居多。据《元史·耶律秃花附忙古带传》记载,耶律忙古带在元世祖时受命征讨云南,后“遥授云南诸路行中书省左丞,行大理金齿等处宣慰使都元帅,卒于军”。耶律忙古带死在云南,其亲戚、部属也大都留在云南,一般认为云南契丹后裔就是这支契丹军队定居云南的结果。在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榔村建有一座蒋氏宗祠,祠堂的正门朝东,这与辽代建筑都为东向相一致,保留着契丹族朝日的习俗。正门的两边有一副对联:“耶律庭前千株树,阿莽蒋氏一堂春。”说明阿、莽、蒋三姓都是耶律氏的后裔。 云南契丹后裔保存着珍贵的家谱资料,这些资料都明确记载他们的祖先是契丹耶律氏。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蒋家云所藏《勐板蒋氏家谱》记载:“蒋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机,创建辽朝,为金所灭。后裔以阿为姓,又改为莽。在元初,随蒙古军队南征有功,授武略将军之职。明朝洪武年间,因麓川平缅叛有功,分授长官司,并世袭土职。后又经历数代,改为蒋姓。”保山市施甸县由旺乡木瓜榔村蒋文良藏有《施甸长官司族谱》,其开篇诗言:“辽之先祖始炎帝,审吉契丹大辽皇;白马土河乘男到,青牛潢河驾女来。一世先祖木叶山,八部后代徙潢河;南征钦授位金马,北战皇封云朝臣。姓奉堂前名作姓,耶律始祖阿保机;金齿宣抚抚政史,石甸世袭长官司。祖功宗德流芳远,子孙后代世泽长;秋霜春露孝恩德,源远流长报宗功。”这本族谱中还有一幅“青牛白马图”,描绘的是有关契丹族起源的古老传说:远古时有一个男子骑着白马沿土河而下,又有一个女子坐着青牛驾的车沿潢河而下,相遇于两河交汇的木叶山,在此结为夫妇,这就是契丹族的始祖。他们生了八个儿子,繁衍成为契丹八部落。但是,除了这些家谱资料,还没有别的史料能证明云南契丹后裔的始祖是耶律阿保机,这很可能是后人为了光大门庭的附会之说。即使是耶律忙古带也不能被证明是云南契丹后裔的直系祖先。 现在可考的云南契丹后裔始祖是阿苏鲁,据《大楼子蒋氏家谱》记载:“有始祖阿苏鲁,任元代万户。及至明代洪武十六年大军克复,金齿各地归附,至十八年二月内,始祖自备马匹赴京进贡,蒙兵部官引奏,钦准始祖阿苏鲁除授施甸长官司正长官职事,领诰命一道,颁赐钤印一颗,到任领事。”阿苏鲁死于明永乐二年(年),其墓地在施甸县甸阳镇大竹棚村东山,立有“皇清待赠孝友和平一世祖讳阿苏鲁千秋之墓基”碑一通,是清道光癸卯年(年)十二月四日由蒋氏子孙重修。碑右起第一行最后有一个于义为“长官”的契丹小字,就是这个所谓的契丹小字给 除了上述得到证实的两个较大的契丹后裔群体外,在我国各地还分布着一些未经证实的契丹后裔,陈述先生指出:“(天津)宝坻县有‘耶律各庄’,至今村人多刘姓。从辽朝以来,耶律译刘。那么耶律各庄刘姓旧户的先世,很清楚地是契丹人。”(见《大辽瓦解以后的契丹人》,载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编《中国民族问题研究集刊》第5辑,年)另外据最近的新闻报道,在西安市长安区有一个耶柿村,多户村民中有户、余人姓耶。据说,其“耶”姓来自“耶律”中的一个字,而该村村民所藏一块民国24年的牌匾上,村民署名的姓氏也确实都是耶律。据其世代相传,其祖先是辽代的一位耶律天庆王,而辽代也确实有天庆年号。至今这些人家仍保留着同姓不婚的习俗。在河北省丰南市稻地镇有一些肖姓人家,据其先辈传说,该肖姓是萧太后的后代,而稻地是萧太后种稻米的地方。现在稻地镇附近还有两个村子分别叫做大长春与小长春,据《金史·地理志上》,中都路滦州石城县“有长春行宫。长春淀旧名大定淀,大定二十年更”。同书卷十一《章宗纪三》载,泰和元年(年)正月庚午,“如长春宫春水”。可见,大、小长春两村的得名确实来自金代此地的行宫长春宫或长春淀。长春淀在大定二十年之前名为大定淀,此名是否延续自辽代,至少目前还没有确切史料可证。因为金代的很多行宫都延续自辽代,因此很可能辽代此地也是一处行宫所在,而为金代所沿用。稻地镇的“肖”姓也很可能延续自辽代的“萧”姓,当然现在还无家谱及其他史料(如碑刻和墓志等)可考。 ★★★★★★★★★凤凰网历史:让历史照亮现实 ★喜欢这篇文章?欢迎转发至朋友圈或您的好友。 ★对本文有想法?回到首页,在“发送”栏输入观点。 ★想看更多猛料?点击页底阅读原文,移步凤凰新闻客户端。 -------凤凰新闻客户端,天天有料!------ 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