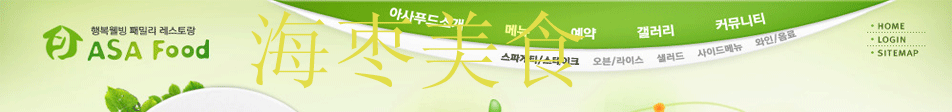|
他默默仰望天空,又是一个夕阳残照的黄昏,宽敞的卧室里依然那样沉静…… 毛泽东半躺半靠在床上,不知一本什么书吸引了他,他已经一个多小时一动不动了…… 小孟坐在沙发上,翻阅着当天报纸,也许是这细微的声音惊动了毛泽东,也许是毛泽东感到了疲劳。他在床上转了个身,顺手把书放在一旁。 正翻看报纸的小孟,大概是护士职业养成的习惯,毛泽东这一不大的动作和声音,令她立马察觉。她顺着声音望去。此时毛泽东正看着她,她刚要站起来,毛泽东却向她做了个手势,把手向下按了两下,意思是让她坐下来。然后毛泽东用他那浓重的湖南口音问道:“报上都有些什么新闻啊?读一段听听,不过,我可不要听什么大批判的成果,要听新闻”。说来也巧,当时小孟也正在看一段新闻,主席的这个要求,正中下怀。 “您要听新闻,这儿正好有一段,我正想做个记号,等您不看书的时候,读给您听听呢”。 “噢,一个想读,一个想听,巧合,巧合,你就读读看。” “新华社长春年4月21日电:最近,在我国东北吉林地区降落了一次世界历史上罕见的陨石雨。今年3月8日下午,宇宙空间一颗陨石顺地球绕太阳公转方向,以每秒十几公里的速度坠入地球大气层中。由于这颗陨石与稠密的大气发生剧烈的摩擦,飞至吉林地区上空时,燃烧、发光、成为一个大火球,于8日15时01分59秒在吉林市郊区金珠公社上空发生爆炸。陨石爆炸后,以辐射状向四面散落。”读着读着,小孟突然发现主席坐了起来,这可是从来没见过的事。 记得有一次,唐闻生送来一份文件清样,读主席接见外宾的名单,因为这个外国代表团是文艺团体,而且有xx夫人参加,所以列上了江青的名字。小孟读完名单后,主席点头同意。后来,秘书问起此事:“主席听到江青名字,没有提出去掉?” “没有啊,反正我是念了江青的名字。” “也许主席没听清吧,他一般不会同意江青去接见外宾的。” 好多次读文件、读报纸,主席都是听听而已。一般他总是静静听着,很少发表什么不同意见,也很少改变或卧或坐的姿势,所以小孟感到,主席对给他读的东西,多半没有什么大兴趣。 而这一次,主席坐起来听了。小孟感到有些奇怪,忙放下手里报纸,准备去问主席有什么事,但主席又是用手势制止了她,并说:“读下去,我在听。” 小孟又接着读起来:“大量碎小陨石散落在吉林市郊区……最大的三块陨石沿着原来飞行的方向继续向西偏南方向飞去……最后一块陨石在15时2分36秒坠地时,穿破1.7米厚的冻土层,陷入地下6.5米深处,在地面造成一个深3米,直径2米多的大坑,当时震起的土浪高达数十米,土块飞溅到百米以外……最大的三块陨石,每块重量超过了公斤,最大的一块重量为公斤,大大超过了美国收藏的目前世界上最大陨石的重量(公斤)。这次陨石雨,无论是数量,重量和散落范围,都是世界上罕见的……” 小孟读完这段消息后,又开始读另一段新闻,主席马上说:“小孟,就读到这里吧,不用再往下读了。”毛泽东边说边穿上拖鞋,小孟上前搀扶,他慢慢地向前走去。看来,毛泽东被一种情绪笼罩着,他的脸上现出一种思虑,一种不安,一种激动。毛泽东在屋里走了几步,让小孟把窗帘打开。这又是很少有过的要求。毛泽东站在窗边,望着那夕阳渐落的天际,望了很久很久,望得那样出神。 小孟见主席转过身来,便问道:“主席,天上怎么会一下落那么多石头呢?太巧了,还没伤人。” 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回答小孟的提问:“这种事情,历史上可屡见不鲜噢,史有明载的就不少,野史上的更多了。” 看来今天主席很有兴致,他又问小孟:“这方面的记载你见过没?你们家里人有什么说法?” 小孟摇摇头,她也只能摇摇头,因为她对此确实了解太少。 “这方面的记载我没见过,小时候听我妈讲,在我们家乡的一个村边,一天夜里,突然掉下一块大石头,有磨盘那么大。后来这块石头又被风刮走了。咳,都是瞎说,我才不信呢。” “噢,你妈妈讲过这样的事,你还不相信。” “我是不相信,您能相信?” “我相信噢,中国有一派学说,叫做天人感应。说的是人间有什么大变化,大自然就会有所表示,给人们预报一下,吉有吉兆,凶有凶兆。” 毛泽东说到这里,稍稍停了一下,然后接着说:“天摇地动,天上掉下大石头,就是要死人哩。三国演义里诸葛亮、赵云死时,都掉过石头,折过旗杆。大人物、名人,真是与众不同,死都死得有声有色,不同凡响噢。” 毛泽东说这些话的时候,带着少有的感慨,少有的激动。毛泽东似乎压抑了自己的激动,转换了个平静的语调:“不过,要是谁死都掉石头,地球恐怕早就沉得转不动了……” 毛泽东又在屋里走了几步,然后坐在沙发上又问小孟:“我说的这些,你信不信呢?” 小孟看了主席一眼,不假思索地回答:“我还是不信,那全是迷信,是古人瞎编的。” 小孟说完后,似乎又觉得没把握,她也很想听听主席的看法。于是,她又好奇反问:“大人物要死的时候,天上会掉下大石头您真信吗?” 毛泽东没有马上回答,他沉思了一会儿才说:“古人为什么要编造这些?”像是回答又像提问。 陨石雨这则消息,后来在民间老百姓那里,确实引起了不少传说,不少议论:“这陨石雨,可是百年不遇,听说落下了三块大石头。这三块大石头,就是说中国必有三个大人物要归天了。” “可不是嘛,三个领袖,周恩来、朱老总、毛主席,都是年逝世。” “那块最大的陨石,多公斤,就是象征着毛主席……” “那些小的陨石,就是指唐山大地震死的那些人。” “还真灵验呢。” “你不能不信,有道理,我看也是这样。” 年底陨石雨的消息,还在人们中间这样议论着,解释着。 年4月22日,毛泽东听到陨石雨消息的这一天下午,他不止一次站到窗前,望着渐渐昏暗的天空,每次时间都很长很长。仿佛那神秘昏暗的天空上,有谁书写了只有他才读得懂的文字。 唐山大地震发生之后,年7月28日凌晨,毛泽东安安静静躺在他那张宽大的木制床上。他那均匀的呼吸,安详的脸庞,那微微张启的双唇,使小孟感到毛泽东今天睡很舒坦,她放心了。 自7月中旬以来,毛泽东的睡眠总体情况不佳。本来,多少年了,包括那些远逝的战争年代,毛泽东的睡眠就是个大问题。国事、家事、天下事,搅得他常常彻夜难眠,他苦苦地思索,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在屋里来回踱步,就这样,送走了一个个黑夜,迎来了一个个天明。当然,这种情景是指他早已过去了的壮年时期。为了能入睡,曾想了各种办法。睡前散步,看书看报,吃安眠药,由医护人员按摩,这已经是多年来所采用的办法了。 进入80高龄的毛泽东,入睡,更成了难以解决的大问题。小孟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之后,也常常为他的睡眠而发愁,使他能睡好觉,成了小孟的一个很重要的护理任务。不然,如果他睡不好觉,必然要有一系列连锁反应,脾气烦躁、饮食不好、心肺病、脑系科病加重。自小孟进中南海以来,在她的记忆中,毛泽东每天都要服安眠药。说起来也很有趣,小张、小孟,再加上毛泽东,三个人每天都服一种药,有时毛泽东看小孟吃药,便说:“怎么你们也服安眠药?看来是近朱者赤噢,受了我的传染。” 小孟边吞药,边说:“那可不是,现在吃安眠药都成了瘾,不吃简直睡不了觉。” 当然,小张、小孟服药的目地,是为了抓紧时间休息,每次一共四小时的睡觉时间,若不马上入睡,就很难保证一定的睡眠。 毛泽东服安眠药已有多年的历史,甚至对药已产生抗药性,有时不得不超剂量地服用,方能生效。为此小孟曾对他说:“主席,您天天吃安眠药,会不会产生副作用?听说,总服这种药对身体不好呢。” “孟夫子说得对,可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之前,只能用这种办法噢,任何东西吃了都有正、副作用,只要正作用大,那就可以取之。”毛泽东很难一气睡上四五个小时,能连续睡上两三个小时也就很不错了。 今天,看到毛泽东睡得好,小孟心里简直是一块石头落了地。不然,她又要在本子上写下“7月28日1点~4点,睡眠不好”的记录了。看见毛泽东睡得那么酣畅,小孟忽然想起了以前秘书曾给毛泽东提的建议:“主席,您睡觉之后,是不是可以由护士长来看着您睡觉,护士长比我们的经验多,更会护理。” 毛泽东听了秘书的话,摆摆手说:“不行,我不放心。” 小孟当时听了这话,心里感到奇怪,有什么不放心呢?打针都可以,护理着睡觉不行?一年多来,小孟倒是发现了毛泽东的一个特点,毛泽东身边用的人,都是他自己认识的人,他熟悉的人,他自己用惯了的人,他就信任,不是他自己认识的人,他一般不同意用,而且他也不喜欢身边有很多人。 小孟又想起另一件事:有一段时间,小孟感到毛泽东总有一种寂寞孤独的情绪笼罩着他,有时卧室里,大厅里总是让人感到一种沉闷,缺少活力,缺少欢声笑语,毛泽东自己看来并不喜欢这样,所以他自己除了读书、批文件之外,常常让小孟、秘书给他讲点笑话,而小孟又不怎么会讲,一个笑话也不能讲多次啊。这样,她有一次,便也给毛泽东建议,我看您应该多找几个护理人员。省得您一睁眼,不是小张就是小孟,人多了,热热闹闹的,今天小张给您讲讲这个,明天小王给您讲讲那个,小张、小冯、小李,都来说说笑笑,那多好。省得您这儿老那么静。毛泽东听了小孟的建议,马上回答说:“静有静的好处,动有动的麻烦,还是那句老话,甘蔗难得两头甜嘛。” 小孟听了毛泽东的话之后,也摸不透他是怎么回事,也就不再提出这样的建议。今天,小孟又出现了这种想法。她想着想着,便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忽然,小孟觉得有人在用力摇她的椅子,她被惊醒了,马上站起来,发生了什么事?耳边传来了玻璃震动的哗哗的响声。她发现卧室里的窗帘正在抖动。她往毛泽东的床上一望,看见他依旧躺在那里,很踏实,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只不过,已经睁开了眼睛,神态像是在想什么。 当小孟还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事情时,护士小李、小俞已从卧室门口进来,实际上是急忙跑进来的。只听小俞慌里慌张地说:“小孟,地震了,大厅里的窗户震得好响。主席怎么样?没事吧?” 按平时规定,她们不经允许是不能随便进入毛泽东卧室的,但今天情况特殊,也顾不得这些了。 也不知是谁的主意,小孟她们几个,从毛泽东床边的小柜子里拿出一条床单,几个人一人抻一个角,撑在毛泽东床上面,为的是怕天花板上掉下什么东西砸着他。她们一声不响地抻着,几分钟过去了,毛泽东又睁开了眼睛,翻了翻身,他好象忽然发现了自己头上面的那条床单,那条白色的细棉布床单在他头顶上面抻着。他略微转动头,向上面,向左右看看,他有些奇怪了,微微一笑,然后说:“怎么?抻床单做什么?” 小孟听见毛泽东笑着发问,便马上回答:“主席,刚才发生了强烈地震,小李他们吓得不得了,赶快跑来,保护您呢。” 毛泽东听了,似乎觉得十分好笑又好玩。他不慌不忙地说:“地震了,越震我倒睡得越香噢,这叫地震不醒安如山嘛。” 小孟说:“我们都紧张坏了,您还有心思开玩笑。” 小俞说:“主席,这次地震厉害得很,比邢台那次明显多了。” “总有一天,会天塌地陷,自然规律么,不用怕。” “您什么都不怕,我们可害怕死呢,可能还要有余震呢。”小李也补充了这么一句。 “怕也好,不怕也好,我看你们抻着单子倒没必要。房子塌下来,一条单子能顶住?”毛泽东做了个落下来的手势,他用手向下挥了两下,几个工作人员才把单子放下来叠放在一边。她们也觉得自己的行为有些莫名其妙。 大约4点59分左右,张耀祠来到毛泽东的会客厅。他通知小张小孟: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发生强烈地震。根据预测,近期很可能还会有余震。主席目前住的房子不太牢固,需要马上搬家,搬到新建的房间去。那所房子安全些。 毛泽东现在住的房子,被称为游泳池。游泳池的住所是60年代用毛泽东的游泳池改建的,房子的四面都有宽大的玻璃窗,毛泽东卧室里的窗户位置很高,平时全用白色帷幔挡住。中南海里的工作人员和一些熟悉毛泽东的中央领导同志,都知道毛泽东的住处叫游泳池。“游泳池”已成了毛泽东住所的代称。这所房子,他已经住了十几年了,据测不甚牢固,所以又给他盖了新房,早在地震之前就几次劝他搬家,但他始终不肯。 唐山大地震后,小孟根据张耀祠的意见对毛泽东说:“主席,汪东兴、张耀祠都来过了,他们讲了这次地震的情况.还讲您现在住的这所房子不太结实,可能还要有余震,希望您赶快搬家。” 毛泽东听了之后,对搬家的事没表态,只是紧接着问:“这次地震情况怎么样?有没有简报?” 小孟听到毛泽东询问有关地震的情况,她便赶紧把刚刚送来没多久的一份简报清样拿来给他读了一遍:“……我国河北省冀东地区的唐山、丰南一带,7月28日3时42分发生强烈地震,天津、北京市也有较强震感,据我国地震台网测定,这次地震为7.5级,震中在北纬39.4度,东经.1度,震中地区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毛泽东听了之后,显出一种少有和焦虑,小孟赶紧说:“您不怕,我们还害怕呢,您也不替我们想想?” 小孟故意用这话激毛泽东,没想到这办法还真灵,毛泽东听了这话,没摇头也没摆手,而是闭上眼睛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你们怕,那就搬吧。” 毛泽东终于被说服了,他同意搬家的消息,几分钟后就传到了汪东兴、张耀祠那里。二十多分钟后,搬家开始了。所谓搬家,其实,比一般人搬家简单多了。那所房子,虽然毛泽东一直末搬进去住,但一切都是按随时赤住在管理着,每天打扫卫生,开窗换空气,调节温度,里面一切设施齐备,只要进来就能住。 年7月31日上午,毛泽东搬进新房。这是唐山大地震之后的第三天,但在这里住了不到40天,他就永远离别尘世。 除了极少数的人之外,大多数的人始终认为:毛泽东每天日理万机,夜以继日地工作着。毛泽东永远是神采奕奕,精神矍铄。毛泽东总是如人们在书报上看到的照片那样,经常伏案执笔,批阅文件,在会议室里开会,在工厂家田头视察…… 直到年9月9日,人们才在不知所措的茫然中结束这想法。 其实人们从报纸上,从荧光屏上,从一切宣传窗口中,都看不到毛泽东晚年真实的工作情况。人们只知道,领袖人物,特别是早已被神话了的毛泽东,在决策着国家的一切,在主宰着人民的命运。毛泽东的一举手、一投足,都会对历史酿成巨大的波浪,他的任何一个意念,都会形成滔滔洪水,一泻千里。 在中国这样一块特定的土地上,在20世纪70年代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毛泽东具有特别的权力,特别的威望。他在占全世界四分之一的人们心中,是生命、是希望、是光明、是永远不落的“红太阳”。 人们没有完全猜错,毛泽东直到生命最后时刻,依旧在工作着,只不过他的工作方式、工作环境已截然不同了。 有一批国民党的将领要特赦。关于此事的文件,名单在年12月份就送到主席这里来了,请主席批阅。主席很快就进行了批阅,主席批阅之后,便把文件放在了柜子里,按常规,要等年春节时再正式发下去。 快到年元旦,有一天主席忽然向秘书提起文件的事:“关于特赦的文件发下去了吗?” “没有,应该是春节前发。” “为什么等春节?可以在元旦发嘛,既然决定了,我看早发比晚发好,人家可是度日如年噢。” 毛泽东的最后日子里,他总是去做他觉得应该是他做的工作,包括不断地会见外宾,只要秘书工作人员转告他,外宾请求接见,毛泽东从不拒绝,既使身体状况很坏。在他的头脑里似乎总是盛情难却,而没有量力而行。 最后一次会见巴基斯坦总理布托就是一例。布托已经来几天了,一直等待毛泽东会见,但由于主席身体状况不允许,所以一直没有安排。当布托马上要离开中国,又一次提出见毛泽东时,主席的秘书便不得不把这种要求向主席报告,果然,主席毫不犹豫地点头同意。其实,当时主席刚吃了安眠药,正犯心脏病,但主席依旧同意安排。因此,才出现了接见时面部表情麻木,直流口水的样子,也因此泄漏了毛泽东身体有病的绝密,这已是无法隐瞒的事实。 病魔缠身的毛泽东感情依旧细腻丰富,依旧惦念着亲人,怀念着故交,关心着朋友。女儿来看他,他会久久地深情拉着她的手,用他不清晰的语音叙别话旧。朋友来看望他,也会引起他的欣喜。他在最后的日子里,也曾关心过金日成。 也许,毛泽东与金日成有着特殊友情,有着特殊情感。毛泽东生日时,曾对金日成送来的大苹果久久凝视,寄托一种异样的情思。当毛泽东听说金日成眼睛患病时,特意派曾给他治过眼睛的唐由之大夫去给他治病,那几天晚上,每次都有金日成治病的电报发来,主席总是认真地看。在朝鲜,在这片并不十分遥远的国土上,牵动着毛泽东的情感。 年9月8日晚,就在毛泽东离开这个世界的前几个小时,他还要来了日本三木武夫的电报看,他在离开这个世界的最后时刻,他的心,依旧在想,依旧在思索,他的眼睛,依旧在看,依旧在环视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他不甘心退出,他不愿意退去,他要竭尽全力。 毛泽东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直至他的昏迷—年9月8目晚上八时十分。毛泽东的身体日渐恶化,这是医生们,周围的工作人员早已看到了的事实,而且已是无可挽回的趋势。 十年动乱,林彪出逃,陈老总、周总理相继去世,一系列的事件对毛泽东来说,不能不是一次又一次的沉重打击。虽然,作为一个领袖,他对一切都很有远见,但他也毕竟具有常人的肌体,他的生理机能也早已开始退化。 年5月12日毛泽东会见新加坡总理李光耀。这次会见,使小孟、小张大为紧张。本来,因看到主席精神尚可,才同他讲了李光耀总理要不要全见的事,他当即答应会见,这已是常规了。 那天上午,主席的理发员小周给他理了个发,又刮了脸。在会见前一个小时,小孟从主席专用的大衣柜里拿出了那套灰色的毛式服装。 “主席,您今天还穿这套衣服吧?”小孟说。 “就穿这个,不穿这个,穿哪个嘛?”主席点头回答着。 小孟帮主席脱了睡衣,换上中山装,穿好后,又前后左右地看,抻抻拽拽把衣服拉得平平整整。看毛泽东接见外宾之前的样子,小孟反而感到有些新鲜:头发整齐,服装笔挺,显得精神多了。 平日的毛泽东,多数是躺在床上,多数是穿着细白布睡衣。头发不理,很有些不修边幅,简直使小孟就感慨不到他是个万众瞩目的国家领袖。 “您现在才像个主席了,平时,您哪儿像个主席呀。”小孟象是在开玩笑地说。 “他就是扮成个主席呢,一扮就像,别人谁也扮不像。”小张刚刚从外边走进来,也打趣地说。 “我去接见外宾,就像演员登台,哪有不化妆的?”主席也开着玩笑。 时间到了,小张小孟一边一个,搀扶着毛泽东,走到游泳池会见大厅。他刚刚坐下来一两分钟,李光耀已由华国锋陪同来到大厅,小张小孟把主席扶起来,她俩赶紧退后,隐到屏风后面,为的是不让录像里留下工作人员搀扶的情景。但主席刚刚站起来与李光耀握完手,扑通一下就坐下了。当时小张小孟在屏风后面看得很清楚,不约而同地小声“呀”了一声。会见只有一两分钟、寒暄几句,便匆匆结束。 小孟小张很知道主席的病情,他经常两腿发软,无法站立,这次突然坐下,是实在无法支撑的结果。早知这样,就不让主席安排这次会见了。张春桥从他前面走过了,姚文元从他前面走过了,王洪文也从他前面走过了,华国锋……吴桂贤、倪志福、许世友一个又一个的政治局委员们都是从他面前过去了。毛泽东只是似看非看的望着他们一个个身影,他是那样无动于衷、无情可动,是他未从病态中缓解过来,还是不想去思考这眼前的事情,人们不得而知。 但当叶剑英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他抬起了那双显得又沉又重的胳膊,他的手颤颤地抖动了几下,嘴微微地动了一下,细微得让人难以发现。 还是小张看出了毛泽东所表达的意思,她毕竟是太熟悉毛泽东的一切了。毛泽东这些动作表示,他想与叶帅说话,小张的分析是正确的。 小张走到已过去的叶帅身旁说:“叶帅,我看主席是想和您说话,您去问问看。” 叶帅点点头,又走到毛泽东身边。他这次离毛泽东很近很近,叶帅俯下身来,低下头看着毛泽东,毛泽东的眼睛突然显得明亮起来,他那本是黯然无光的眼睛,很久没有这样的光芒了,眼睛是心的窗口,他的心里一定翻动着什么,但他的嘴已是力不从心了。只见他嘴唇在张翕着,但很难听也他的声音。叶帅拉着毛泽东的手,紧紧握住,不停地向他点头。 毛泽东对叶帅讲了些什么?是对他表示了永久的别离之情,还是有什么事情需要交代,还是对永远过去了的岁月的回忆? 毛泽东对叶帅曾有这样的评价:“吕端大事不糊涂。”叶剑英曾在中国革命的许多关键时刻,起到了别人所不能代替的关键作用。毛泽东自知已不久于人世,他在这个时候,或许会意识到,中国又将面临一个关键时刻。如果真是这样,是否又要叶帅这样一个关键人物来起关键作用呢?此时,叶帅能拉住毛泽东的手,但无论如何,也拉不住毛泽东的生命。 毛泽东,从8月底直至他谢世,多次昏迷,多次抢救,在昏迷与抢救的过程中,他渐渐向着另一个世界走去。谁也无法真正知道,濒临死亡的前几分钟,几秒钟,他真实感受是什么,除非他死而复生过,那他自己也许会说清楚。 9月8日晚7时,小孟来接班,几天来,政治局的常委及委员们,一直在轮流值班,医务人员一直在身边观察毛泽东的病情,量血压、测脉搏、导尿、听心脏、输氧气,不停地进行着。 这时江青也来了,这时,她的到来,不用经过毛泽东的批准,毛泽东已没有批准与不批准的精力了。她可以作为家属随时来探望。江青来探望,并不在毛泽东的眼前,而是在其身后,因为在这之前,江青出现的时候,毛泽东只要清醒时,总是有反感烦躁之情,为了不引起新的刺激,江青就在背后看看。 7点10分时,毛泽东的呼吸急促起来,小孟过来,低头给主席按摩胸部,主席用很低的声音说:“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医生赶紧把氧气的管子放在他的鼻子处。他用手去拽,肯定是不舒服,过了几分钟呼吸开始平静起来,这时,医生看见主席的鼻孔里有一点嘎巴儿,就把输氧管先拿下来,用棉花签给他弄出来之后,又给他戴上输氧器时,他就一点反应也没有了,又是处于极度的昏迷。抢救,抢救,四个多小时的抢救,但一直是昏迷,他再也没有醒来。 他的最后一句话是对小孟说的:“我很难受,叫医生来。” 年9月9日零时。毛泽东卧室通往大厅的走廊通道上,那宽宽的通道里,电视荧屏正显示着毛泽东心脏跳动的情况,一道波浪式的曲线在起伏,抖动。 中共中央政治局的所有常委、委员们,毛泽东身边所有工作人员,都在静静地注视着荧光屏上的这条曲线。他们没有表情,没有话语,没有判断,没有猜想。 华国锋静静地目视前方,王洪文眼睛在不停地睁闭。张春桥一副冷静的神情,汪东兴眉头微皱。 ……平静、木然、无言、沉默,这也许只是外在的表现。 0时10分,荧屏上的曲线突然变成一条直线,一条微微抖动着的直线。 委员们,工作人员们,家属们,一切在场的人们立刻打破了沉寂,向前倾身,睁大眼睛,死死地盯住荧屏,小声议论。迟疑着,判断着。这条直线,这条由曲线变成的直线,表明什么?几分钟过去了,荧屏上一直是一条直线,一条仍在微微抖动着的直线。毛泽东先停止了呼吸,继而心脏停止了跳动。 一个护士从毛泽东卧室出来,走得那样轻,向外边等候的人们说了一句:“主席去世了”。 她的话说得那样轻,几乎看不出她嘴的动作,仿佛这声音是从口腔内部发出的。 人们一齐走向卧室。十几分钟之后,医生们退去了,政治局的委员们退去了,家属也退去了。 汪东兴、张耀祠告诉小孟小张,留下来把主席遗物整理一下。委员和家属们都开会去了。 小孟拿起床头小桌子上的那几份文件。那几份主席最后批阅的文件,放在文件袋里。她又拿起那本依旧打开的“三木”书,轻轻地把它合上了。在这本书上,留下了毛泽东的最后目光,留下了他最后的思索,留下了他最后的情感。 小孟向毛泽东的遗体望了一眼,她又把目光投到了那本“三木”的书上。她仿佛要在这本书上找到主席留下的目光,留下的思索,留下的印迹。 她悄悄地把主席读过的最后一本书,放在床侧的书柜里。她放得那样轻,那样小心,那样心细,生怕自已的稍重的动作,会抖掉毛泽东在上面留下的痕迹。 小孟把主席最后换下来的内衣、内裤,叠得平平整整、放在床头的小柜子里。小孟把主席用过的铅笔拿起来,细细地看着,小周给主席削好的这支铅笔永远不会再被人用了。她真想拿去做个永久的纪念,但她这种念头闪现的同时,一种指责声已在她耳边响起:“你怎么可以这样,不行,不能办这种事情。” 她把铅笔轻轻拿起,又轻轻放下,依旧放在小桌子上。在主席床头的书桌上,她发现一本厚厚的鲁迅选集,不由得翻了几下,忽然发现里面有一封信,一封没有装在信封闭里的书信。这是李敏写给毛泽东的信。 注爸爸: 您好,您近来身体怎样?女儿十分惦念,您让我读的这本鲁迅选集,我已经都读完了,什么时候,我想和您谈谈这些杂文的看法,这本书里您画了不少符号,写了一些评注,我都仔细看了,但有些地方还是不明白什么意思,我想抽空找您问问。 祝愉快 您的女儿李敏 年4月15日 小孟把这封女儿李敏给父亲的信夹在书里放回了书柜,她们做了些简单的整理就不知还要整理什么了…… 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 |